
一
我的家乡在祖国南端温暖的海滨,大片的榕树林枝叶婆娑地穿梭着记忆的层层迷途。在童年,我的祖父每天晚上都会在榕树下,一边吸着香烟,一边给我和一群小孩子讲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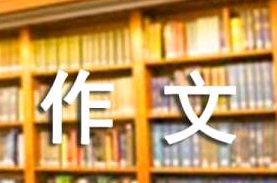
在他的讲述里,我成了北冥之地的神鱼鲲,从冰冷的海域向南溯游而上,鱼鳍化为缤纷的羽毛,在松树林、杉树林、榕树林中自在穿行,最后扶摇直上九万里高空,绮丽的翅翼映出天边的最后一片晚霞。
我听得心思荡漾。那时我已经进入学校,逐日行走在庸常的平地上,不然我将会霍然而起,以北冥的古老力量在云上飞行,穿过遮天蔽日的榕树密林,途经迷蒙的云梦大泽,沿着奔腾怒吼的金沙激流,攀上巍峨壮丽的雪山屋脊。在羽毛映出的霞光里,向那位两千多年前的文学天才放声赞唱。
十多年后的夜晚,我在那棵又添了几多年轮的榕树下对小表妹讲,蝴蝶翩跹,晓梦浮生。那时明月融进骨血,江河潮汐暗生。
小表妹听得津津有味,不断催促着我再讲讲。
她不知道,这个故事的作者是庄子,而我的想象力,在榕树下听故事的那些夜晚里,就开始奇迹般疯长。
二
春天,我们穿得像一群仙鹤,沿珠江寻找一棵开花的树。阳光在河滩上铺陈开来,江水像镶了一层闪闪熠熠的金边。
在我的幼年,沿着河流往东方走,有棵高大的木棉树,春天时玲珑的橘红花串遮天蔽日,香得人觉都睡不着。那时我每每经过,总要驻足凝望,不经意间,经年的芳香就早早沁入心田。
此刻,辽阔的河滩上,那棵花树姿容丰美,朋友们嘴角噙着淡淡的笑,我闭上眼,艳阳恍恍。又呆呆靠在树下看风景,对岸妩媚,孤山清晰可见;天上的游云,白色翻涌。间或有人轻轻吟道: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风过叶响,一瓣娇嫩的木棉花悠悠落下,像一阵红色的轻雾。
当花季过去,再次沿着江岸漫无目的地行走时,我什么都忘了。
或许只要在花树下轻轻徘徊,逍遥地躺下看看流云,我连自己都会忘了。
三
在深秋进山。三千米深林,内中立着一座破观。二十多年前,有个道长来到这里,在旧址上一点点重建。暴雨过后的这座山,漆黑苍虬的古树,金光灿灿的雨水滔滔铺陈开来,映出一点远古的秘境意味。
我攀着道长说这说那。我问,渺渺沧海,人怎么才能逍遥一生?他说,来喝茶,喝茶。
同行的皆是我的师辈人物,笑着开口解困,问观里还缺不缺米,是否要送些过来。
山中入夜极早。天空在白日里是澄澈的泛白浅蓝,又渐渐过渡成深蓝,最后彻底融进浓墨一般的厚重夜色。小观没有电灯,如豆的小火苗在暗云中轻轻摇曳。夜里骤雨突来,林涛如怒,窗外声浪滔天,滚滚似孤猿长哀。
这样的夜里我们聚在一起。他们讲述彼此熟稔的前半生,诗酒狷狂,半生冤祸。我在一旁听着,手里的书恰好看到黄永玉写“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,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”,犹如当头棒喝,不免一阵心惊肉跳。
忽然有人说,梁兄吹一段埙吧。“扑”一声,烛火吹熄,只有窗棂隐隐透着一点水光。远处暴雨嘶吼,仿若万马奔腾下山。他起音极低,几乎只是唇齿间的气息,曲调像多年前大风的哭泣。我一开始无感无触,只握着热茶,把身上厚重的羊毛披肩复又围紧。就这一首曲子,循环往复,像静水下的暗涌,有时候要腾出水面,又被狠狠压住了,有时候汹涌起来,在快要席卷岸边的时候忽然退下去,都静默得快听不见了,又从海底的一声呜咽再起。
四下萧然。都隐在黑暗里,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泪,却也知道这声音里是千百年的无奈。
那晚我在雨中放声哭泣,披肩都湿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