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中考前三个月,我突然看不见了。不是真正的失明,而是医生说的“用眼过度导致的暂时性视物模糊”。世界变成了一片朦胧的水彩画,所有的轮廓都融化在灰白色的雾气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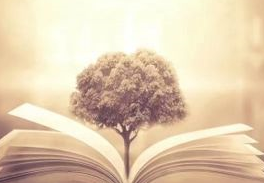
母亲替我请了假。最初的几天,我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同学们放学时的喧哗。那些声音曾经与我有关,现在却像另一个世界的回响。课本上的公式、单词、文言文,都变成了无法触及的遥远符号。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失去光之后,连时间都会变得黏稠而缓慢。
第四天,我摸索着走到院子里。春深了,空气中有樟树新叶的气息。我闭着眼睛坐下,任凭光晕在眼皮上跳动。然后我听到了——不是用耳朵,而是用整个身体听到了这个世界:蚂蚁在墙角搬运食物的细碎脚步声,风吹过晾衣绳时发出琴弦般的震颤,隔壁奶奶哼唱的古老歌谣像水纹一样荡开。
母亲下班回来,坐在我身边,开始读我课本上的文章。她的声音很轻,有时会念错字,我就笑着纠正她。我们就这样一页页地读下去,从《岳阳楼记》到《荷塘月色》,那些曾经需要背诵默写的文字,在她的声音里重新活了过来。我忽然听懂了“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”不只是修辞,而是真正的水波在荡漾。
最奇妙的是夜晚。当视觉彻底休息,触觉变得异常敏锐。指尖抚过粗糙的树皮,能感受到生命在春天里的膨胀;掌心接住的雨滴,每一颗都有不同的重量;甚至能摸出月光和路灯的不同温度——月光是凉的,像丝绸;路灯是暖的,像麦粒。
一个月后,视力开始恢复。世界重新变得清晰锐利,课本上的字一个个跳回眼前。但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。我终于明白,那些日子里我并非被光遗忘,而是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看见:看见声音的形状,触摸温度的质地,聆听沉默的言语。
后来每次走过那段日子,我都会想起那个闭着眼触摸春风的少年。他让我明白:真正的光明不在于眼睛能看见多少,而在于心是否愿意打开更多的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