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离乡的列车在午夜出发,父亲执意要送。月光如水银泻地,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母亲塞满的行李中,有一包用油纸仔细裹着的乡土,说是可以治水土不服。我笑她迷信,却在那包沉甸甸的土壤里,第一次触摸到乡愁的形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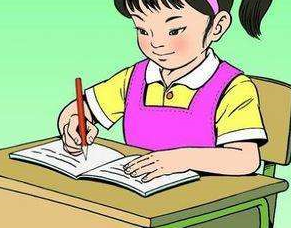
月台上,父亲沉默如铁。这些年来,我们之间的对话大多通过母亲转述——“你爸说钱够不够”“你爸让多穿衣服”。此刻,月光填满了我们之间的空隙,却照不亮那些从未说出口的话。
列车缓缓启动,父亲的身影在月台上越来越小,最后化作月光里的一个墨点。我打开车窗,夜风裹着稻香涌入。忽然明白,这月光走了多少光年,只为照亮一个离人的旅途。
第一站是北方的大学。城市没有稻田,只有钢铁丛林。失眠的夜里,我取出那包乡土放在枕边,恍惚间竟真的闻到了稻香。给家里打电话,母亲说父亲每晚都去田埂上散步。“他说要帮你看看今年的月亮圆不圆。”
寒假归家,惊见父亲鬓角已白如霜。他依旧沉默,却开始学发短信。收到第一条:“月圆了”,我对着手机笑了整晚。那包乡土我一直带着,从北方到更远的南方。每当月光洒落窗前,我就取一点泥土在指尖捻开,仿佛还能捻出故乡的晨露与晚霞。
多年后,我也成了异乡人。在中秋的异国街头,看见华人老人颤巍巍地供月饼拜月。那一刻忽然泪流满面——原来中国人走到哪里,就把月光带到哪里。这光穿越秦汉唐明,照过李白苏轼,如今照着我,还将照向更远的远方。
我终于懂得,当年带上的不是一包泥土,而是一片可以随身携带的故土,一轮永不西沉的月亮。它让我无论行走多远,回望来路时,总能看见家的方向亮着一盏月光。
今宵月色正好,我继续带着这光上路。前路或许坎坷,但只要有月光照亮,就知道自己从何处来,该往何处去。这月光是祖先的目光,是文化的血脉,是一个民族千年不断的乡愁,更是每个游子心中永不熄灭的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