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老宅拆迁前夜,我在阁楼发现祖父的樟木箱。箱开刹那,陈年气息扑面——不是霉味,是时光窖藏后的醇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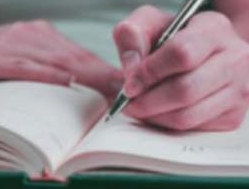
箱中最醒目的是一叠用红线捆扎的信笺。纸已脆黄,墨迹却依然清劲。最上方是祖母十七岁时的照片,穿着月白旗袍,眼角有颗小小的泪痣。照片背面祖父题词:“初见君时,春雨湿金陵。”
我这才知道,祖父祖母竟是自由恋爱。在1937年的南京,师范男生邂逅女中学生,他们在秦淮河畔谈诗,在紫金山下论画,直到战火逼近。
“愿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11月,“若不能,则望君珍重,如珍重我们共同的理想。”署名后另附小字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——不是遗憾,是约定。”
翌日问父亲,他才道出往事:祖母家族南迁前欲订婚约,祖父却投笔从戎:“国破如此,何以为家?”他们相约——若生离,则各自珍重;若死别,则此情待追忆。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祖父参加南京保卫战,负伤被救。辗转八年找到祖母时,她已在西南成家。”父亲声音低沉,“祖父终身未娶,只说‘此情可待成追忆’,是两个人的约定。”
我震撼难言。原以为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是李商隐的怅惘,在祖父这里却是庄重的承诺——不是不能相守的遗憾,而是曾经相知的感恩。
箱底还有一封信,是祖母1985年寄来的。那时祖父已卧病,祖母得知后写信:“忆君年少墨香,如在目前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我亦珍重至今。”信纸上有水渍晕开,不知是泪是茶。
原来他们用一生诠释了“可待”——不是被动等待,而是主动珍藏。将最深的情感酿成追忆,不是因为它不完美,恰恰因为它太完美,不容尘世磨损。
如今我也到了祖父初遇祖母的年纪。在速食爱情的时代,我格外珍惜这份“可待”的深情——它教会我:有些感情不是为了拥有,而是为了证明人间值得;不是故事的残缺,而是生命的完形。
樟木箱合上的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: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深意,不在于“追忆”而在于“可待”。那是用一生去守护的信念——无论是否相聚,真心付出过的情感,永远在时光里熠熠生辉。
就像祖父祖母,他们从未在一起,却从未真正分开。因为最美的爱情,或许不是朝朝暮暮,而是明知此情可待成追忆,依然选择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