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家住在染料厂隔壁,整个世界都是蓝色的。
不是天空的蓝,也不是海洋的蓝,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化学品的蓝。早晨醒来,枕头上落着蓝色尘埃;晾晒的白衬衫,总会莫名染上蓝边;就连下雨天,屋檐滴落的都是蓝色的泪。同学们叫我“蓝孩子”,说我的呼吸都带着颜色。我憎恨这无处不在的蓝,它像一种宿命般的污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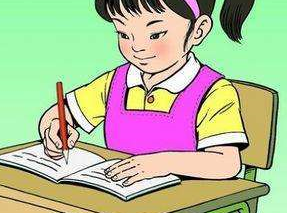
父亲在染料厂工作三十年,他的指纹是蓝的,指甲缝是蓝的,连吐出的烟圈都带着蓝雾。我拒绝让他参加家长会——我不想让人知道,我就是那个被蓝色浸泡大的孩子。青春期的自尊心像一张白纸,最怕被染上洗不掉的色彩。
高二那年,染料厂终于停产。最后一夜,巨大的染缸被排空,父亲在厂门口站了很久。那天晚上,他破天荒地给我看了他的“作品集”——原来三十年里,他每天下班都会画一幅画:今天调试的普鲁士蓝,昨天新配的孔雀蓝,三十年前第一次接触的靛蓝……每一幅画下面都写着日期和配方,还有当天的心情。
“1999年6月12日,女儿出生,调出最像天空的蓝。”
“2008年5月13日,汶川地震,全厂加班做救援帐篷的染料。”
“2016年9月1日,女儿上初中,不肯让我送。”
最后一页是空白的,只写着一行字:“所有的蓝都会褪色,唯有记忆越染越深。”
父亲告诉我,当年他可以选择调去白班,却主动申请管染缸。“因为你妈妈最喜欢蓝色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望着墙上母亲的遗像——她穿着蓝裙子,笑靥如花。母亲在我三岁时病逝,父亲再未续弦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原来父亲三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那些染缸,是在用他的方式调制思念的浓度。而那些我曾拼命想要洗掉的蓝色印记,是他能给我的最深沉的爱——他把整个天空的蓝、海洋的蓝、世间所有的蓝都搬到我身边,生怕我忘记母亲最爱的颜色。
现在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,我都会骄傲地说:蓝色。不是因为它象征永恒或自由,而是因为它最像爱的本质——无处不在,无法逃离,深入肌理,用最沉默的方式,诉说最漫长的守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