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外公的秤,是条老街最后的良心。
秤杆深褐,秤星已磨成隐约的白点,如散落时空的碎银。每逢集市,他必郑重取出,以软布轻拭——那姿态不像在擦秤,倒像在拂去蒙在时间上的灰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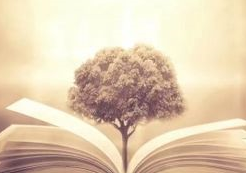
“看准了,十六两。”外公将秤砣稳稳定在最后一颗星上,秤尾不偏不倚。顾客满意而去,留下硬币在木箱里清脆一响。那声音,是诚信最朴素的回响。
“知道为什么是十六两吗?”某个黄昏,他指着秤杆问我,“前面十三两是北斗七星,后面三两是南斗六星。缺一两叫‘损福’,缺二两‘伤禄’,缺三两‘折寿’——老祖宗的秤上,压着整个星空。”
我怔住。原来每一笔公平交易背后,都有星辰在见证。
后来,老街对面超市开张,电子秤嘀嗒作响,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人们渐渐绕过外公的小摊,奔向更“高效”的所在。他的秤,像不合时宜的文物,在喧嚣中沉默。
直到那天,一个中年人提着从超市买的“足秤”干货,气冲冲来请外公复秤——“八两!”他瞥一眼,平静道。人群哗然,纷纷回家取货复秤,无不短斤少两。外公不言,只将他的老秤摆在最显眼处,像升起一面不倒的旗帜。
风波过后,外公的小摊竟又热闹起来。人们说,在这条日益虚拟的街上,只有他这里还“称得起”实实在在的重量。
我终于明白,外公守护的不是杆秤,而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法则。当世界在算法的迷宫里狂奔,当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日渐模糊,总需要一些人不改其度,以肉身作为最后的标尺。
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王冕以梅花自况。而我的外公,和他的秤,不求喝彩,只愿将那份名为“诚信”的星辰重量,留给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与人间。
那压秤的,不是铁,是星斗;不是交易,是天道。在万物皆可量产的年代,他固执地守着最古老的手艺——为人心定盘,让天道归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