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外婆的院子里有一口老酱缸,每年腊月,她把黄豆蒸熟,铺在竹席上,让它们在北风里慢慢长出金绿色的霉。我捂着鼻子问:“这臭东西能好吃?”外婆笑得像一弯新月:“好东西都要等。”三个月后,酱成,揭开盖子,酱香劈头盖脸地涌上来,像黄昏的炊烟。我蘸了一口,咸鲜滚过舌尖,一碗白粥瞬间有了灵魂。外婆用木勺敲我脑门:“知足吧,皇帝也就这个味。”那时我尚小,第一次感到“够了”竟是一种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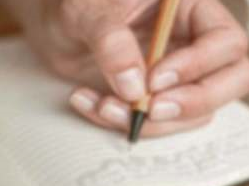
高三那年,我把这种甜弄丢了。同桌刷题到凌晨三点,我却在十二点停笔,心里生出罪恶的轻松;可一旦陪他熬到四点,第二天上课又昏沉得想撞墙。我像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陀螺,不知该停在何处。焦虑在胸腔里发酵,长出绿色的霉,却不是酱的香味,是苦。深夜,我对着卷子掉泪,觉得分数永远不够,排名永远不够,自己永远不够。
五一放假,外婆捎来一瓶新酱。我拧开盖,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,像一只温暖的手,把我从漩涡里拎出来。我忽然想起酱缸里的秘密:豆子若“知足”于温暖,只会腐烂;必须被冷空气逼出霉,再被盐逼出汁,才能成就一味。原来人生也需两次“逼迫”——先逼自己走出去,再逼自己停下来。前者叫不知足,后者叫知止。
回校后,我给自己定了“酱缸法则”:每天额外完成两套小题,但十一点必须睡;每周前进二十名就够,剩下的时间读诗、跑步。我不再盯着别人的夜灯,而是盯着自己心里的刻度。六月,我考进理想的大学。通知书到那天,我把外婆的酱涂在面包上,一口下去,咸香四溢。我笑着对母亲说:“我够了。”母亲反问:“真的够了?”我点头,又摇头——够的是这一阶段的努力,不够的是下一程的山海。
如今,每当我深夜写论文卡壳,就泡一碗酱面。蒸汽爬上眼镜,我闻到岁月发酵的味道:它提醒我,知足不是句号,而是逗号;不知足也不是惊叹号,而是省略号。我们在逗号上蓄力,在省略号上奔跑,把每一口平淡都酿成醇厚,把每一次“够了”都变成新的“还不够”。酱缸静静立在记忆深处,像一轮隐形的月亮,照着我——学会知足,也学会不知足,在咸与鲜之间,把人生慢慢酿成自己喜欢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