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粥锅里的月光
凌晨五点的厨房总有响动。母亲系着蓝布围裙站在灶台前,白瓷碗里盛着刚剥好的莲子,蒸汽在她鬓角凝成细珠,落进衣领时,她正用木勺轻轻搅着砂锅里的粥。
上个月我生了场病,夜里总咳得睡不着。朦胧中感觉有人坐在床边,手背贴着我的额头,带着皂角的清冽。后来才发现,母亲枕头边多了本翻旧的医书,在 “止咳偏方” 那页夹着干枯的枇杷叶 —— 是她清晨去后山摘的。
降温那天放学,校门口的人群里,她举着件厚外套张望。风把她的围巾吹得猎猎响,毛线帽边缘露出的发丝沾着雪粒。我接过外套时触到她的手,冰凉的指尖在我袖口系扣子,却把暖意全缝进了衣襟。
上周整理书桌,在旧书包的夹层里摸到个油纸包。打开来,是块压得扁平的桂花糕,糖霜早就化了,却还能闻到淡淡的甜。忽然想起那是去年期中考试的早晨,她塞给我当早餐,说:“考不好也没关系,妈给你留着热粥。”
此刻砂锅里的粥正咕嘟冒泡,莲子的粉糯混着米香漫出来。母亲把盛好的粥端上桌,碗沿还留着她的指温。原来母爱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是粥锅里的月光,是枕边的药片,是无数个被忽略的清晨与黄昏里,悄悄为你亮着的那盏灯。
这世上最暖的粥,永远熬在母亲的锅里;最安稳的眠,总在她掖好的被角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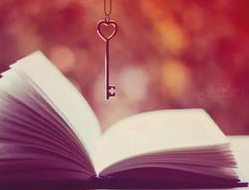
《毛衣里的春天》
母亲总在暮春时节开始拆毛衣。阳光斜斜地爬上阳台,她坐在藤椅里,苍老的手指勾着毛线,像在解开一个个温暖的结。那些旧毛线垂落时,我仿佛看见自己成长的年轮,一圈圈舒展在她膝头。
记得儿时每个倒春寒的清晨,床头都会魔术般出现叠好的毛衣。领口永远缝着棉布衬里,因为母亲说我的脖子像含羞草,经不得半点摩擦。六年级那次春游,我赌气不穿她新织的枣红毛衣,结果在山里冻得发抖。傍晚回家时,却见那件毛衣正在晾衣架上滴水——原来她怕我着凉,竟冒雨把毛衣送到了学校门卫室。
去年整理衣柜,发现箱底压着件袖口起球的鹅黄色毛衣。那是高考前夜母亲连夜赶制的,前襟还缀着四颗木扣子,她说"四"谐音"胜"。我忽然想起那个夏天,她如何在台灯下忍着腱鞘炎的疼痛,把毛线绕在肿胀的手指上。灯光里翻飞的银针,织进去的何止是经纬线,还有她说不出口的忐忑与期盼。
如今母亲的眼睛已看不清针脚,但她仍坚持每年拆洗旧毛衣。她说毛线越拆越软和,就像记忆,经过岁月的揉搓反而更加清晰。上个月我偷偷学着她的手法织了条围巾,歪歪扭扭的针脚间,漏进了整个春天的阳光。当我把围巾轻轻围在她肩上时,她眼角的皱纹忽然聚成了小漩涡——那里面旋转的,分明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给她画的"笑脸太阳"。
《母爱如粥》
凌晨五点半,厨房的灯准时亮了。
我在睡梦中听见瓷勺碰在砂锅边沿的轻响,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。这声音太熟悉了,像一支温柔的晨曲,告诉我妈妈又在熬那锅红枣小米粥。
厨房的门没关严,飘来一缕若有若无的米香。我裹着被子坐起来,看见妈妈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。她系着我初中时送她的蓝底白花围裙,袖子挽到小臂,正用木勺慢慢搅动锅里的粥。砂锅里的小米在沸水中翻滚,几颗饱满的红枣浮浮沉沉,像红色的小船在米白色的海洋里航行。
"醒了?"妈妈回头看见我,眼睛弯成月牙,"再睡会儿吧,粥快好了。"她的声音里带着刚醒的沙哑,却依然温柔。我看见她眼下淡淡的青色,想起她昨晚加班到十点才回家,今早五点又起来给我熬粥。
粥的香气越来越浓,弥漫了整个房间。妈妈盛了一碗递给我,吹了吹热气:"小心烫。"我捧着碗,指尖触到她冰凉的皮肤。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,在晨光中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喝下去的瞬间,从喉咙到胃都暖了起来,连呼吸都带着红枣的甜香。
这碗粥里藏着妈妈的爱。她记得我胃不好,要喝小火慢熬的粥;她知道我不爱吃姜,所以从来不在粥里放姜丝;她甚至留意到我最近学习到很晚,特意多加了两颗红枣。
母爱就像这碗粥,看起来平淡无奇,却饱含着最温暖的滋味。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表达,只是在一个个平凡的清晨,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我:你永远被爱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