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家堂屋的墙上,有一块颜色格外鲜亮的方形印记。父亲说,那里曾挂着一幅年画,是奶奶的嫁妆。而在我记忆里,那块墙皮之所以新,是因为别处都被灶台的烟火熏黑了,唯有那里,被一盏灯守护了十几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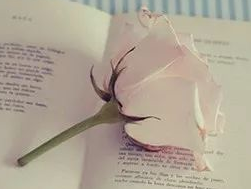
那盏灯,是一盏煤油灯。
童年关于夜晚的记忆,是昏黄、摇曳的。母亲在灯下纳鞋底,针尖偶尔在灯焰上一过,便是最亮的刹那。我的影子被投在墙上,巨大而模糊,随着火焰舞蹈、变形。我就在这影子里写字,常常嗅到头发被灯苗燎到的焦糊味。那时,电是山外遥远的概念,我们村是地图上被遗忘的角落,夜晚的唯一光亮,就是这盏飘忽的灯。它照得见近处,却照不亮未来。
改变,是从一根电线杆开始的。
那个春天,开进山的卡车惊醒了沉睡的村庄。人们围着那些水泥杆子,像围观巨人的骨骼。当第一根电杆在我家门前立起时,奶奶拄着拐杖,摸了又摸,喃喃道:“这东西,比老松树还结实哩。”
通电那晚,全村人都屏息站在屋里。当开关被按下,白炽灯的光芒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瞬间,整个屋子鸦雀无声。我被那从未见过的、斩钉截铁的“白昼”惊呆了,继而爆发出巨大的欢呼。母亲仰着头,看了那灯泡很久很久,直到眼里蓄满了光,她才轻声说:“往后,晚上也能做针线了。”
这束光,是一个开始。
电来了,路就通了。路通了,山里的山货、药材就能变成钱。父亲买了磨面机,再不用驴拉石磨;母亲用电商直播,卖她缝的虎头鞋;我的课本在灯下清晰如昼,那盏煤油灯,则被收进了柜子,成了时代的注脚。
去年除夕,我家装上了最亮的LED灯。明晃晃的灯光下,年夜饭蒸腾着热气。电视里唱着欢歌,窗外,太阳能路灯将村路照得宛如星河。
我望着墙上那块曾经被煤油灯守护的印记,忽然懂得了脱贫的真正含义。
脱贫,不是数字的增长,不是文件的传递。它是让一个孩子不必再在摇曳的灯焰下读书;是让一位母亲不必再就着微光缝补生活;是让一座村庄,从此拥有了不眠的夜晚和清晰的明天。
它从一束“光”开始,最终照亮的,是无数人的未来。那盏退休的煤油灯沉默着,但它见证了一切——我们如何从一抹昏黄的火苗出发,最终,迎来了照亮整个世界的黎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