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和故乡的距离,是1678公里。这是列车时刻表上的数字,是18小时硬卧的辗转,是手机天气预报里两个城市的温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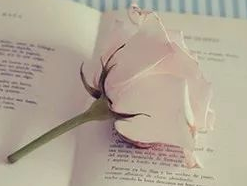
我曾以为这就是全部。
十六岁那年,我像逃离监狱般逃离那个胶东半岛的小城。火车启动时,我看着站台上母亲缩成一个小点,心中涌起的竟是自由的狂喜。在大学里,我努力擦除身上的乡土印记:改掉黏稠的方言尾音,拒绝母亲寄来的海货,甚至刻意忘记小城春秋的湿度。
距离被我亲手拉成一道鸿沟。我在微博定位里炫耀大城市的坐标,视频通话时总把镜头对准繁华的街景。母亲在那头说:“窗外的合欢花开了。”我敷衍着,心想这种小情小调多么微不足道。
转变发生在一个加班的深夜。我揉着干涩的眼睛走向茶水间,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甜香——同事在泡槐花蜜茶。那一刻,1678公里土崩瓦解。我仿佛被拽回老家的庭院,看见祖母踮脚摘槐花的身影,听见蜜蜂的嗡嗡声,舌尖泛起童年偷吃蜂蜜的甜。
我冲回工位,疯狂搜索故乡的新闻。弹窗跳出一条:“旧城改造,文化路梧桐开始移栽。”文化路!那是我走了十二年的上学路,春天梧桐絮飘进教室,秋天踩碎落叶如踩碎星光。而现在,它们即将消失。
我第一次拨通视频不是为了展示,而是为了追问:“妈,文化路的树真的都要砍吗?”母亲愣了一下,随即兴奋地切换镜头:“你看,我今早去捡了片最大的梧桐叶,给你夹在书里!”
隔着屏幕,我看见那片梧桐叶静静地躺在《诗经》第167页。突然想起那句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,原来两千年前的乡愁与此刻并无不同。
今夜,我再次查看导航——距离仍是1678公里。但我知道,真正的距离不在大地之上,而在心灵之间。当我在超市认出故乡的苹果,当我在异乡的雨中想起小城的雨季,当我终于承认想家不需要羞耻——距离就在那一刻归零。
我和故乡的距离,是用思念编织的尺子。一头扎进北京的马路,一头系着老家的梧桐。每一次心动,都是它在丈量我离最初的自己,还有多远。